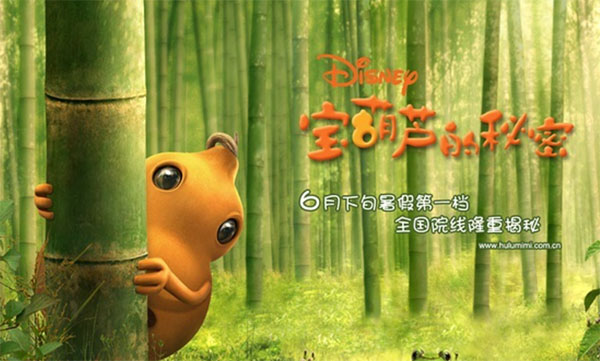情比金堅,海枯石爛——讀《我們仨》有感
讀完《我們仨》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無限惆悵。就好像聽著一個溫柔的老人平淡的訴說著她的家事,可是每個字、每句話都包含著她深沉的愛,每個停頓都充滿著她無限的思念。我才明白“人間沒有單純的快樂,快樂中夾帶著煩惱和憂慮”。
《我們仨》是楊絳先生92歲高齡時的作品,說是隨筆集,更像是一本回憶錄。楊絳先生的筆觸總是平緩的,溫暖而洋溢著淡然的味道,像秋天的落葉,像冬日的暖陽,平靜而柔和。就像她和錢鍾書的愛情,和錢瑗的親情。
在那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楊絳先生和錢鍾書自由結(jié)婚,一起前往牛津讀書。為了照顧吃不慣房東家伙食多少錢鍾書,連嫌棄蠶豆“殼太厚,豆太小”的楊絳甚至學會了為他做紅燒肉。同樣,當楊絳在牛津生孩子時,錢鍾書一天來醫(yī)院看望她四次。出院后,“大阿官”錢鍾書也專門包了雞湯伺候她,從牛津開始為她做了一輩子早餐。在他們意見不合時,往往雙方會先保留意見,因此他們從不爭吵。進入暮年,他們?nèi)匀槐3种?ldquo;探險”的習慣,一起散步,探索新事物。他們也會爭,爭著讀女兒的家信。甚至還相互理發(fā),錢鍾書用剪刀,楊絳用電推子。在人生這條漫漫長路上,他們相互扶持,相互鼓勵,成為互相的精神支柱。他們的感情從無轟轟烈烈,而是清風吹拂,晚波蕩漾。
1937年,牛津出生了第二位中國寶寶——錢瑗。錢鍾書抱著她看了半天,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錢瑗也說“和爸爸最‘哥們兒’”。錢瑗在日后的生活中,處處表現(xiàn)出與爸爸相似的地方:翻書時兩根指頭夾著書頁,甚至走路姿勢都極為相像。錢瑗每次書寫家信都用記號筆,只因錢鍾書高度近視。在這三口之家中,楊絳先生似乎才是那個需要被照顧的一方,錢鍾書離家還特地囑咐錢瑗“照顧好媽媽”。小時,錢瑗陪媽媽走夜路,大了,錢瑗住院時給媽媽寫信還不忘教她做一些簡單的飯菜。錢瑗生為女兒讓父母欣慰,身為學者、教師又讓他們驕傲。錢瑗在職期間修訂教材、熬夜備課,若不是生病,她不知還要多久才愿意退休。錢瑗對于二老來說,不僅僅是女兒,更是一位好朋友。他們之間的親情,就像冬天的手爐,天氣愈冷,手爐愈暖。
可惜,“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曾經(jīng)的歡樂,而今的寂寞,天人相隔,往事皆隨風遠去。當初的我們仨,此刻,獨留楊絳一個形影孤寒。楊絳先在命運面前是渺小的,任憑命運的種種,她早已釋懷。因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