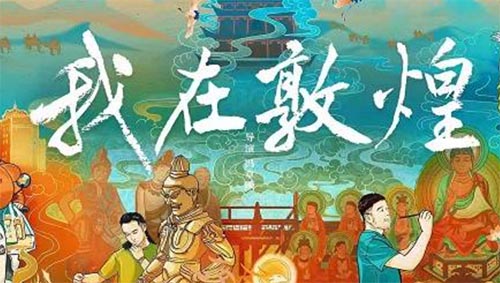一見敦煌定終生,錦瑟友年華,青絲暮白發——題記
她從繁華的都市走來,扎根于貧瘠的西部小鎮;她從熱鬧的人群中走來,懷抱在孤寂的風沙與月夜;她從開放的當代走來,蜿蜒在歷史的深厚罅隙間。從青春少艾,到垂暮之年,她身行一例,勝似千言。
樊錦詩作為敦煌的女兒,一直走在保護文物的最前列位置。她堅持創新,積極倡導文物國際交流與合作,不斷引入先進的保護理念和保護技術,構建了“數字敦煌”,讓敦煌用全新的方式長存,讓更多的人隨時隨地都能看到敦煌獨一無二的美。在她的身前是無數的勛章與贊美,而她身后的風沙與苦難往往是不被人們所熟知的。
在《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本書中則揭露了她背后不為人知的一面。書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樊錦詩與自己的孩子關系的描寫。她的身邊沒有親人幫助,在孩子出生幾天后自己的丈夫才挑了一副扁擔轉輾來到敦煌。自己因為工作原因,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只能送往親戚家照養。接往自己身邊后,發現當地的教育資源十分落后只好又送往他處。兩個孩子的教育水平受到了影響,時常讓她感到愧疚于心。而她對孩子的唯一要求卻是,不能做壞事,成人后自立,為社會做點有益之事。
她為國之需,忍雙載分居,棄灼灼芳華,一生擇一事,報入敦煌窟。她被人戲稱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改革開放后,她繼續砥礪前行,把前輩開創的事業發揚光大。她舍小家,顧大家,淡泊明志,板凳能坐十年冷。不管是煤油燈下埋首勤學,靠鏡面折射光臨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還是不厭其煩,開展石窟數字化,分析壁畫病害機理,建設敦煌學信息資源庫……她都帶領研究人員樂此不疲,樂在其中,終于在敦煌學的各個領域獲得建樹。
幾代莫高窟人以他們的青春和生命詮釋的正是“堅守大漠、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堅守和奉獻源于對這份事業的熱愛,對遺產保護的責任。正如村上春樹曾說”喜歡的事自然可以堅持,不喜歡怎么也堅持不了。”寓保護于研究之中,寓熱愛于責任之中,成為莫高窟人的自覺,也形成了身居大漠、志存高遠的傳統。從無到有,幾代莫高窟人就是以“舍身飼虎”的精神開拓進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保領域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文化弘揚發展中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空白,結出了一個又一個碩果,為國寶重現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擔當,探索奮進,最終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主力軍。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她令無數有志之士潛心于她的臂膀與擁抱之中,悄悄用霜雪拂過他們的兩鬢,使他們孤身徘徊于浩渺無際的月夜之中。僅僅靠幾代人、幾十年,只能維持她一時的容貌,更需要有世世代代不斷地為她付出,持續地奮斗。而在這期間,有許多莫高窟人在這里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記。常書鴻、段文杰兩位老院長在宕泉河畔長眠,他們所做的貢獻是在敦煌歷史上不可磨滅的。而他們的墓地只若蒼茫天地里的一粒微塵般點綴在荒蕪的大漠其間,甚至連遠處的游客都不會注意到,更不用說短暫的駐足了。他們在未知的黑暗中,用自己赤誠的心,點亮了一絲光芒,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即使遇到了再大的挫折,也終是砥礪前行,永不言棄。
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我們站在時代的節點上,處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最好時期,也立足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既面臨著難得的建功立業的人生際遇,也面臨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時代。樊錦詩先生的“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引導了當代青年的奮斗目標;袁隆平院士的“向前看不要向錢看”啟發了祖國無數新建設者;孔繁森黨員的”甘為人梯,長期鋪墊“更是教導著我們堅守初心,不斷向前。
發展永無止境,奮斗未有窮期。作為當代中國青年,我們應當用行動落實理想,用堅毅守護夙愿,用汗水澆鑄夢想。以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擔當自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奮勇爭先,在國家的脊梁上敲響青春之鼓,在新時代的脈搏上注入自己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