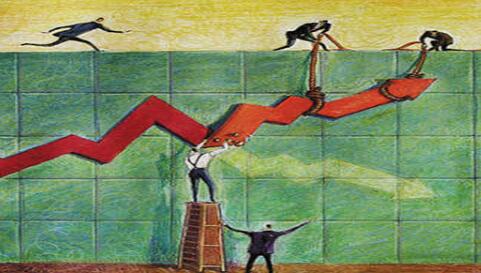余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一個先鋒作家的姿態進入中國文壇,后來卻轉向書寫人道、溫情。進入九十年代后,余華的小說的創作風格發生了明顯變化:從前期尋求語言張力與刺激、敘述風格的陌生化轉向逼近生活真實,以平實的民間姿態呈現一種淡泊而又堅毅的力量。
余華前期代表作品諸如《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都是暴力美學的代表。這一時期余華的作品中充滿血腥、暴力。為什么余華要通過如此犀利的筆墨向讀者展示一幅幅鮮血淋漓的慘劇,一次次展現人性惡的那一面呢?其實我認為余華是借人性的殘忍冷漠來展現人性的真善美,就像天空中的星星,夜空越黑,越能反襯出星星的璀璨。如早期作品《在細雨中呼喊》中做哥哥的孫光平對弟弟孫光林的關愛,馮玉青撫養兒子的堅強,孫廣元與奶奶之間的患難情義,還有在《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中,“我”壓根不認識那死去的朋友,但“我”還是履行著朋友之義,想著自己應該替他守靈,向其母親盡孝,為他掃墓,這都是展現人性的善的那一面。如此也是做到了將暴力與善良完美的融合。除了暴力美學之外,余華的作品中的“灰色幽默”也令我印象深刻。通過荒誕的描寫突出表現了現實生活中的個體與環境的沖突,并把它們不斷放大,帶來喜劇效果的同時也加深了讀者對時代的思考。在《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為了一個不是自己親生的兒子賣血七次,如此用揶揄的方式描寫苦難,無情地揭露現實的虛偽面具和丑陋傷疤不禁引發我們的深思。除此之外,反諷也是余華經常使用的創作手法之一。《活著》名為“活著”,卻通篇充斥著死亡,借書中死亡對官僚主義、大躍進運動和文革等方面都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諸如此類的手法在余華的作品中相互交織,最終為我們呈現出了令人驚心動魄的效果。
余華在《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說:我意識到偉大作家的內心沒有生死之隔,也沒有美丑之分,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處。這使得早期的余華作品中帶給我們的更多是用極其冷靜的方式來展演暴力、血腥和死亡。而后期的余華的作品描繪社會中的人性丑惡面逐漸隱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中的溫和面和人性深處的善良、堅韌,并且也更加關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讓我們感觸更加深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兄弟》中的宋凡平。當無盡的苦難襲來時,他選擇以隱忍來默默承受這一切,苦中作樂,在逆境乃至絕境中不拋棄生的希望,對于親人,他溫情流露,以血與淚書寫生命的頑強。
其實在仔細審視余華作品中,透過其冷酷與殘忍的故事,貼近他那“冷到零度”的敘述,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他在“真實”人生中所展示的能夠穿越殘忍與苦難,欲望與瘋狂的生之意志與溫情的人性之光。